望著嬰兒的雙眼,不自覺得會被他的純真與澄澈剔透所吸引。這麼著望著、看著,仿若喚起內心最初的悸動、最初的愛,一種回歸本心善性的清朗。
是吧,在成長中我們何嘗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中武裝自己、偽裝自己,只是,最後的模樣是自己嗎?
抑或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唯有把自己的安全裝備提升到與他人相同等級,這樣才不會因為自己的純真與樸質,而將自己白白送葬。
但我也要說,其實純真也沒什麼不好,只要找到個適得其所之處。
2009/06/15
2009/05/23
無米樂‧吾米樂
 課堂上以觀看無米樂,來代表中國的農民性格。這次觀看無米樂,已是我第十幾次看這部片。有別於獨自坐在電腦前觀看,跟大家一起在大螢幕前欣賞總是會有不同的感受,而每次的觀看,隨著不同觀眾的組成,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再切入這部片。因為,每一次的笑聲傳遍播放空間或是靜默之處都有所不同。
課堂上以觀看無米樂,來代表中國的農民性格。這次觀看無米樂,已是我第十幾次看這部片。有別於獨自坐在電腦前觀看,跟大家一起在大螢幕前欣賞總是會有不同的感受,而每次的觀看,隨著不同觀眾的組成,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再切入這部片。因為,每一次的笑聲傳遍播放空間或是靜默之處都有所不同。
無米樂一片中主要想傳遞出老農對於現今農村的沒落的反應,但是卻不因沒落而自怨自艾。在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總是不瞭解,為何每個星期爸爸總要千里迢迢的回到金山老家,然後就為了在神龕前燃上一柱清香,向祖先及神明祝禱。我始終不懂,為什麼這柱清香及短暫的默唸會讓我爸爸這樣每週周車勞頓的往返於台北跟金山。
這個問題,在無米樂中有了答案。
在一個「看天吃飯」的環境中,所有的不確定性都在「敬奉玉皇大帝大天尊,賜福給眾弟子,平安幸福,事業順利,五穀豐收,風調雨順,合境平安」中表露無遺。農民無所依恃,能夠依存的除了土地就只有天候。因此,當人面臨無助、生活的不確定性時,信仰變成了唯一能夠支持的信念。當崑濱伯參加地方年度繞境時,看到崑濱伯母拿著香在繞境的行列中虔誠敬拜著,更看到崑濱伯母拖著老邁的身軀,俯下身,一寸一寸的爬過神轎,為的也許僅僅是奢求微渺的神明庇佑。但是,即使天候不佳,穀物欠收,仍是反求諸己、反躬自省。
這一刻,我突然懂了,突然瞭解從小務農的爸爸為什麼今天已經是從事裝潢工作,卻沒有改變他信仰的寄託。因為,在這無所憑恃的世上,隨著爺爺奶奶的過世,透過清香,將爸爸與親人、神明連結起來。而這樣的連結,更給予爸爸精神上支持的力量,也在這個至今仍有「看天吃飯」味道、變化波譎雲詭的社會,尋求一絲絲的精神膚慰。
對於農人,土地,也成了生活中情感連結的一部份。
如果,農民因為有了大筆的土地而想要坐享其成,透過變賣土地來賺取大富大貴,那可以說,農民對土地已死。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根,如果只是因為財富而擁有土地,那麼,這塊土地也將哭泣。但是現在隨著傳統農業的農村益加沒落,伴隨著進入WTO,米價是毫無起色。然而,農民也無所怨言,只是笑笑著說:「褲腰帶勒緊一點。」
問他要上街頭嗎?他們回答:「以前早被日笨人壓迫到不敢有意見,國民政府來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壓抑了心中的反動。抗議?想都不敢想!」
純樸的農民默默的承受著現實的殘酷。
那上街頭的那些人呢?都是那些為私利而出聲的代表們啊…農民上街頭?!你看到的也許都是假象。而農民的身體就像劇中說的,「身體壞了沒關係,但是土地不能讓他荒蕪。」這句話我是特別有感觸。
我大伯,是個終身務農的人,他愛牛勝過生命中的所有。四、五年前卻因右腿膝蓋老化換人工關節,開了三次刀都未見好轉。最後,三年前的仲夏,正值大夥兒農忙之際,不良於行的大伯在一日早晨,飲農藥自盡。
當初我以為是他無法忍受身體的病痛而離開。
但是,今天我終於了解,一個畢生跟土地連結在一起的人,而今卻無力去打理,
任其荒蕪,那在大伯的心中,或許真的是心如刀割。劇中人說:「每天都會很自然的想去田裡巡巡看看,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如果沒去看看,就渾身不對勁。如果農人對土地沒有感情,那他的心已死。」
或許,真正令他想走的原因,是他無法面對其所愛的土地變成今天荒蕪一片、荒煙漫草的光景。而一個農人對其土地無能為力之時,他還有什麼生存下去的理由?
2009/05/22
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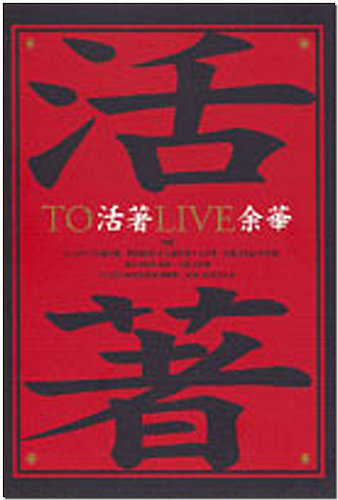
作者:余華/著
出版社:麥田
「春生,你記著!你還欠我們家一條命吶。你得好好的活著!」如果,一個人的存活,只是為了去記住你所欠別人的一條命,那麼,活著是否顯得有些諷刺與悲哀。
文中主人翁福貴,嗜賭成性,從富家少爺輾轉變成流落街頭的乞丐,妻女因此而拋棄離去。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妻子家珍帶著女兒及甫出生的男嬰有慶回家,自此福貴痛改前非,安份守己過日子。但好景不常,1949年正是動盪的內戰時期,福貴被抓去充任國民黨的兵伕,因而結識春生。其後遇到國民黨節節敗退,轉而在共軍唱戲,回鄉之後面臨到共產統治下的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在大躍進中,當上區長的春生開車意外撞死有慶;而後在文革後更遭喪女之痛,但是福貴與家珍都在喪子喪女中活下來。配合著春生受迫害一度想要自殺的念頭,家珍卻道出「你得好好活著,因為你還欠我們家一條命」,更鮮明深刻道出活著是個艱苦而又深刻的事情。
活著,本來是個很簡單的命題,也許只要苦幹實幹、謹守本分,那麼就可以這樣安安穩穩的終其一生。但是,當活在一個你無法掌握的動盪大時代下,那麼「活著」,可不是只有自己就能掌握的了。《活著》帶你體會生命的荒謬,並從荒謬中重新認識「生命」的真正內涵。
科學向腦看:我們正在用還在演化中的腦去理解那演化而來的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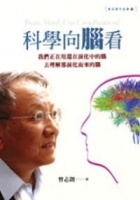
作者:曾志朗
出版社:遠流
「你知道現在鐵路的寬度是由上個上個世紀的兩隻馬屁股決定的嗎?」「你知道地中海的亞歷山卓港在西元前三百年,由托勒密二世下令攔截所有往來的商船,騰錄船上所擁有的書籍因而造就史上的第一座圖書館?」
本書是由前中研院院副院長並專長於認知心理學領域的科學小頑童—曾志朗,集結其於《科學人》科普雜誌中專欄文章而成之著作。文中透過證據說故事、實驗見真章、研究問到底,以及閱讀看門道四個類別,引出不同層面的科學議題。
舉例而言,在華人世界中很容易用「我以為」、「我想應該如此」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中所見到習以為常的事件。然而,科學人卻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驗證所見所聞。好比說見人打哈欠,自己也會不由自主的哈唏起來。也許有人推測是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過高所致,或是與打哈欠者一起感到很無聊的緣故。但是可愛的科學家,卻會大費周章的設計實驗,一一檢視二氧化碳濃度高與濃度低的環境,與無聊是否造成打哈欠。但是實驗結果卻告訴我們,即便在純氧環境中也不見得會少打哈欠的機會,而飛行員跳傘前也可能因為緊張而哈欠連連。
這本科普作品帶著我們穿越時空探索古今人們的智慧,並讓我們用「正在演化中的腦去理解那演化而來的腦」,一窺大腦智慧的堂奧。
走‧光
 偶然的逃離這個習慣的世界,發現仍然運作的世界,當沒有人關心你時,存在便沒有了意義,也不會與其他人產生任何交會或連結。
偶然的逃離這個習慣的世界,發現仍然運作的世界,當沒有人關心你時,存在便沒有了意義,也不會與其他人產生任何交會或連結。
就如同卡緊相扣的齒輪,運行不迭的捷運,每一個指標都發著光說,「看我!看我!」深怕他不夠醒目而讓過路的人們迷失了方向。但其實,在相同奪目引人的指引下,視覺也因為如此強烈地刺激而疲憊了,正如同不斷的高潮下,也分辨不出激情的美妙。
在這些標誌的專家系統指引下,你必須相信他。不想相信?那麼面對的是交通號誌顯現綠燈時,你不敢走;平交道柵欄沒放下,你怕列車衝過來;每天上下班陪你的汽車,可能煞車失靈;公車司機可能打瞌睡;高鐵的軌道上可能有個小螺絲釘鬆了...如果你不願相信的話。
只是,在人來人往中,這些燈箱的光彩炫目,到底是揭示著台北捷運的用心,服務品質第一,抑或是...只是讓人在忙碌的台北生活中,更感受到外來聲、光、色、味的反覆衝擊、刺激、洶湧侵襲下,更顯內心的疏離與寂寥罷了。
漫遊台北的,迷‧茫‧朦‧朧
2009/03/17
那些消逝歷史教我的事
 究竟,在這個無窮迴圈中,何時才能逃出?而今,在這個環境,不論是商紂王的酒池肉林,或是鴻門宴上的觥籌交錯,其實在不同的事件中、時空下,舞台是一批又一批的演員,在一幕又一幕的布幔開闔下,時間向前推移,佈景在更迭汰換中進步。
究竟,在這個無窮迴圈中,何時才能逃出?而今,在這個環境,不論是商紂王的酒池肉林,或是鴻門宴上的觥籌交錯,其實在不同的事件中、時空下,舞台是一批又一批的演員,在一幕又一幕的布幔開闔下,時間向前推移,佈景在更迭汰換中進步。
若然,無論是坤伶、是戲子、是丑角、是說書的,都不過是在不同的時間,上演著相同母題的劇碼。反觀自己,每個人心中的大千世界,被不同的情緒,喜怒哀樂所囿限,為各種慾望所綑綁,以不同的形式、活動、態度來滿足內心各種的求索。是吧!滿足內心的各種慾望是人性的,是原始的,是野蠻的,把每個赤落的慾念,以一種函數的形式,用不同的刺激來滿足。一旦,這種慾望滿足的形式以不敷需求,只得以不斷擴張的可渴望與野獸般的嗜血態度,來填補這無邊無際的內心黑洞。
與其,使這個黑洞無限期的擴張,倒不如讓內心的欲求消融,使自己不為外在的慾望所左右。沈澱自己,是需要經過一番掙扎的,是需要經歷一番身軀的苦痛,以一種以毒攻毒的治療,來將深植於內心的慾望毒瘤,用清瘡手術在內心劃下一刀又一刀的開口。每一刀,飛濺出的血柱,代表著愛、恨、情、仇。唯有以如此深刻的手法,才能讓這早已腐壞潰爛的傷口,與臭不堪忍的膿汁,在汩汩流出的過程中展試著慾望醜陋的原始面貌,傷口才開始有癒合的機會。
2009/03/03
Je t'aime
「流浪是因為沒有方向,還是為了找尋方向,所以流浪。」
他去了巴黎,而她留在台灣。他看著機上窗戶上的倒影,「究竟此去是能將心停泊,還是另一次的遠颺呢?」飛機起飛,她目送著他的離去。曾經交會過、又如此親暱的兩人,再度別離。
臨他上機前,她仍回味著他對她許下承諾的情景。頷首,她晶瑩的淚珠滑落。"Je t'aime"煙火中,排出了對她許諾的文字。「砰!」黑紗輕掩的天空點綴出璀璨的花火。他若無其事的離開,佯稱要去招呼人看茶。那是個遊人如織的傍晚,她正左右顧盼著冷清的樓房,並思忖著街上人聲雜沓帶來的強烈對比。
是個再平常也不過的日子,他帶她來到了都蘭的海濱。海面沈靜無波...to be continued
2008/12/14
那些流逝時光教我的事
 依然金黃耀眼的晨曦,依舊高亢嘹亮的歌聲,仍是屹立不搖的房舍;不同的是迎面吹來的金風不再溫暖,空氣中的濕溽氣味不再嗆鼻,留下的只是一方濃烈的鄉愁。
依然金黃耀眼的晨曦,依舊高亢嘹亮的歌聲,仍是屹立不搖的房舍;不同的是迎面吹來的金風不再溫暖,空氣中的濕溽氣味不再嗆鼻,留下的只是一方濃烈的鄉愁。
依舊是成功嶺,依舊是川流不息的人潮穿梭在烏日站。只是一齣齣上演的劇碼依舊,人來、人往,但演員一波又一波的更迭,看戲的觀眾亦逐漸老去。而時光之流不停歇的將路上的人們以光速把大家向前送去,用一種毫不留戀的態勢。
人們,是有情的,縱然在快速流逝的歲月中,我們仍拼命的、努力的、用盡氣力的試圖把一些甜美、一絲苦澀、一分回憶,用我們的方式,可能是鑿在岩壁,可能是邀月賦詩,可能是秉燭為文,可能是手撫快門;只是期待在稍縱即逝時,留下些什麼。
金黃灑落,帶來了1億5000萬公里外的熱力,鼓舞了冬日中酣睡的旅人。凝視著日頭,頃刻間忽有紙醉金迷之感,訪若只見唐玄宗大宴賓客、酒酣耳熱;又見聞天祥在幽閉深闕中,疾筆振書。但見,101中的觥籌交錯,看守所內的為文作記,何嘗又不是景物雖非而人事依舊呢?
而我在此舉筆,不過也只是胡言亂語一番。恣意仰臥在落葉紛飛的的土地上,仰望著斜陽投射映在楓葉上紅的、黃的、綠的,更有的是一束束光芒射過樹隙,彷若上天傳來的旨意,讓我登時流連其中,久久不能自己,宛在仙境般徜徉在藍天、楓林中,那份氤氳、迷濛,而我在當中迷失了...
沁
 溫暖的空氣中釀著巧克力的芬芳,黃暈的光芒染在沁著笑意專注的臉龐,親切殷勤的招呼著往來的顧客。
溫暖的空氣中釀著巧克力的芬芳,黃暈的光芒染在沁著笑意專注的臉龐,親切殷勤的招呼著往來的顧客。
「我想試吃這個看看」,「那個也可以試試嗎?」此起彼落的聲音穿梭在一間小巧而溫馨的糖果屋中。
「妳有想過這家店的老闆是用怎麼樣的心情開這家店呢?」
「我有想過耶!」答話者的臉上漾出欣喜興奮的神情,「老闆可能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做這些東西,也喜歡吃,而且不是想把他經營的很大。就可能只是把自己的喜悅分享給別人吧!」
「會被嘲笑的夢想,才值得去實現!」我倒是覺得,與其擔心被別人嘲笑,倒不如可以把自己的理想落實在一方小天地中,讓這一小塊地方的人也能分享著跟自己一樣的喜悅。
啜飲著香醇咖啡,沈醉在口中逐漸消溶的巧克力帶來的幸福感,依偎著交流彼此內心的悸動;也許,一個溫柔的擁抱,能消融冰封的玫瑰。
2008/11/30
某一天@醫院
十一月十七日
 發現,原來只有寫作才是治療我鄉愁與愁緒最好的方式。
發現,原來只有寫作才是治療我鄉愁與愁緒最好的方式。
今天,當大肚山腰的風依然吹拂,日頭以不怎麼毒辣的態勢,在綠蔭的阻攔下,也只得俯首稱臣。而在台北盆地那端,牙科的器械依然以規律而高頻刺耳的聲響運作著。醫師仍如同面每一個冰冷機器般,口裡冷冷喊出,「31,現在以9mm植體植入」,「幫我拍41跟43」,此起彼落的叫喚聲正井然有序的應和著。如果說醫師必須對每一個病患病患保持冷靜而幾近冷血的態度才能使其完美無瑕的完成手術,那麼對病人及病人家屬似乎已經接近崩潰邊緣的殘酷。
特別是,當手術台上躺著的是妳母親之時,是妳的至親血肉之時。其實,我明白每個人所接受的苦難,皆是源於每個人不同的業(karma),有不同的功課必須完成。但是當面前是妳自己的至親摯愛,我不知道、也沒有把握能把自己的平等心處理得那麼好。
身體依然不自由,思想於靈魂卻能穿越命令的禁錮、堅實的圍籬,而使我自在的遨遊於人間。看著一個又一個影子在單槓上奮力的掙扎著,想著這究竟是為自己、為別人、為國家,還是只是...只是為了生存顯的更有意義、不致虛度而做出的無聊可笑之舉?
或許在我簡單腦袋中,無法理解這錯綜的道理,只能夜夜在鼾聲、長官斥喝聲中,試圖讓自己在一成不地日子中,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










